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提出,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文明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学术界从不同理论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然而,我们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根本方法论指导,我们才能准确、全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进而拨云见日、洞察真理。
文明存续的物质依附性
文明一词,从词源学角度看,是城市化、城镇化、市民化,指特定的城市化、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和样态的总和。特定文明形态的出现和彰显集中体现为对一定城邦或国家的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道德践行和文化信仰的一致化。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的产生、存在和演变,源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而一定的市民社会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文明蒙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老的中华文明所依附的自然经济及其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停滞状态,在于几百年未有更新的宗族化血缘化的封建人身依附状态。“文明蒙尘”带来的警示就是,任何文明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形态,而特定社会形态的根基就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依附性存在的一定的文明新形态的飞跃,离不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新形态和物质交往新形态的飞跃。中国新时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自信,就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的提出、确立、发展和壮大的整个物质演变过程。当下,文明存续的物质依附性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确保站在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高点上。中华民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加持下,能够实现对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和发展,进而创立出更新更发达的物质文明,方能真正牢固确立属于中华民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演变的历史传承性
中华民族当下在面对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同时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破乱局、立新局,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否发挥自身作用的时代之问。面对时代之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用“五位一体”协调文明发展体系开启了革命和建设新征程。“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动展现和历史传承。以“四个现代化”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文明内核,是马克思主义文明体系的鲜活明证。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新形态”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指导中国传统古老文明的演变,实现在新时代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基础上的新生和与时俱进。以古迹建筑遗址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以语言、文学、艺术和中医药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明,这些传统文明中所承载的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整体包容性质的文明观,是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构建的宗主—殖民地文明体系的超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旧文明的超越。为此,我们必须牢牢确立基于中国新时代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华化的文明新体系,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明体系的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优秀文明观的深度融合。
文明发展的辩证否定性
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于:在唯物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一切都在过程的流变中实现自身的否定,实现事物的前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新事物,就是对一切旧文明的否定。中世纪文明把古代文明、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资本主义文明则把中世纪文明一扫而光,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所谓“文明世界”。所谓的“文明世界”的本质就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运行体系,一切只有服务于资本的文明才能得到延续,一切不符合资本需要的文明都会被炸毁。基于《共产党宣言》相关论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诉求就是要在发展理念上“以人民为中心”取代“以资本为中心”;在劳动过程中以“联合体劳动”否定“异化劳动”;在政治理念上以实质民主扬弃形式民主;在政治组织上以民主集中制取代专制独裁或无政府主义。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还要实现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基于封建等级尊卑基础上“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的保守自闭文明的否定,用共产主义文明的标尺去衡量、祛除一切“可怕的异教神怪”的文明桎梏。
文明互鉴的世界历史性
“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如果前述侧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文明主体的特殊性分析,那么,文明互鉴、文明共生共荣,则是侧重于其包含的普遍性。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其中,文明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显然,这三个阶段所共有的普遍性就是基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日益实现了统治阶级群体的财富自由、社会制度和人民交往的规范化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多元。社会主义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带有上述所言的文明的普遍性维度。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共生理念,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根本追求和世界文明史演进的正确方向,引领文明潮流。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共荣实践,提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互相尊重、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世界文明互鉴的精神之源和深层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百年实践不断体现出自身作为新文明的异质性和超越性,进而彰显出自身作为人类社会新形态、新事物的本质存在。这种异质性和超越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持续浸染和润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深入交汇融合,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征程中为世界文明历史所提供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我们发展好中华文明、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就一定能够推动文明的创造性发展,一定能够实现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尚小华,作者系五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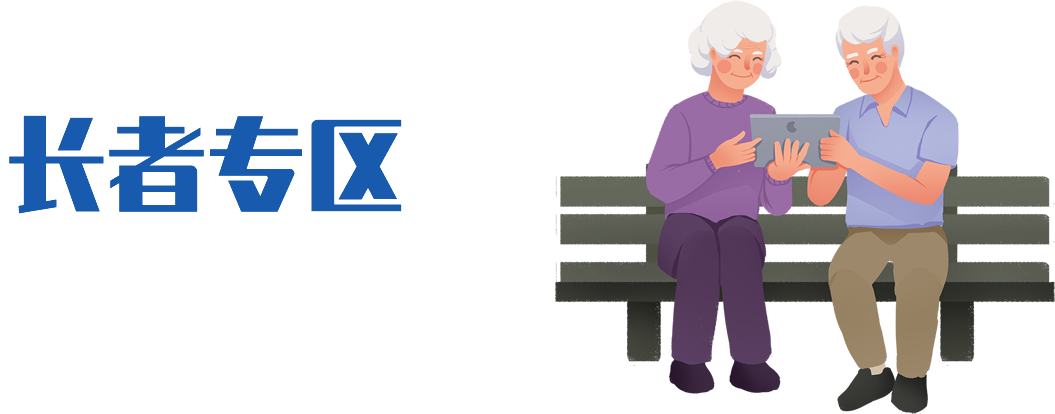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